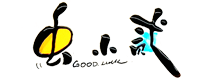等下一个天亮

我低头看手里的杂牌MP4,好久前下载的视频,不知第几次播放。似乎连这个小破机器都受不了乏味枯燥的工作,画面一帧一帧,不停定格--我也因此看得更清楚。他狭长的眉毛,他海蓝色的眼睛,唱到动情处嘴角细小的皱褶。他站在灯光中央,高举双臂,迎合台下海浪般翻涌的欢呼,用稚气未脱的声音呐喊:"Yeah,IloveChina!"
这是Darrel来中国开演唱会的现场,网友小A用手机把全程拍摄下来。在Darrel论坛的视频区,招摇地标榜出"和小D的第一次亲密接触"。
"他碰了我的手,我的手!"小A在视频框下注释着,后面加了一串惊叹号。
画面有些晃动。歌迷的尖叫,充斥歌曲的前奏和Darrel轻声说出"Thankyou"之后很长的时间。
画面又晃了几下,Darrel看向这边,便晃得更厉害。
屏幕暗下来,四处归于安静。我叹声气,把播放器和耳机胡乱叠折在一起,塞进裤子的口袋里。
太阳未落尽,晚霞被渲染成漫长寂静的深红色。茶楼的灯都已大开,辉煌的光芒,让木招牌上"深原茶楼"四个古香古色的字显得稀落很多。顺着茶楼周围的铁栅栏,爬下成片软趴趴的绿色藤蔓,像围墙密密包裹住茶楼。却依然能感到从外面倾泻进来,污浊的空气。
深原茶楼坐落在这座城市很有名的公园里。逐渐有客人进来,坐定后用小指扣桌面,招呼服务生上茶。
阿Z走向这边,拍拍我的肩:"愣着干嘛,快招呼客人啊。"
"哦。"我应着。拖沓着步子给客人倒茶、上茶点。心里却不安宁,有几次走神,把茶水倒在外面,慌手慌脚地擦桌子,给客人道歉。
"我来吧,我来吧。"阿Z从我手里接过壶,陪着笑给客人上茶具。我束手束脚地站在一旁,用手紧捏衬衫下摆的衣角。
画面晃得很厉害。Darrel看过来,似乎咧开嘴角。耀眼的白牙齿。光束被切成一段一段,投向这边,散发出丝样的质感。
周围蓦然腾空的巨大尖叫。人群使劲向前挤。一只手出现在屏幕里,微微张着,伸向Darrel。
我紧紧闭上眼睛。
送走最后一批客人,已接近午夜。
茶楼前的喷泉已停止喷涌,大理石砌成外围,鱼儿换气时,留在水面上一个个细小的水泡。
"你有心事吗?你今天状态可不太好。"阿Z坐在喷泉旁,望着我。
"没……没有啊。"我敷衍地应付他,把脸侧过去,越过他的头顶,看向喷泉。
他揉揉头发,用发胶撑起来的造型被弄得一团糟。"八成是Darrel,"他轻声说,拉着我的手把我拉到眼前,"你啊,迷恋他到这个程度,这可不好。"
我不说话,沉默了一阵。夏末乍起的风,已有了凉意。我缩紧身体。
"开学后不常来了是吧。"阿Z转换话题,笑起来。我便跟着他一起笑。有些不知所措,望着面前的喷泉,浮在水上的月亮。
过了一会儿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包装完好的桂花糕,放进我手心。
--忙一晚上了,快吃吧。
这是假期的最后一天。知了发出最后几声虚弱的喊叫,有声嘶力竭的意味,夜又归于沉寂。我带着一身汗渍回家,倒在床上,呼吸快要把我掩埋了。半梦半醒间又挣扎着爬起来,收拾明天入学要带的物品。巨大的行李箱,乱七八糟堆满衣服。我在床褥下翻出Darrel的照片,塞进钱包里。
爸妈常年不在家,我很小就学会照顾自己。所谓"照顾",不过是凭借桶装方便面和Darrel度日。我所担心的,只是从明天开始,在禁锢的寄宿制学校里,无法时刻关注Darrel的动向和去茶楼打工。
后半夜才睡着,因为一个凌乱的梦不得安宁。转天很早被闹钟吵醒,顶着乱蓬蓬的头发,拖着一堆行李,转乘好几辆公车去学校。
双眼一直浮肿,揉搓时能挤出泪来。公车拐弯时,我紧紧攥住行李箱的长把手,在拥挤的人堆里尽量保持平衡。却总是不小心碰到别人,低头忍受白眼,小声道歉。影子在阳光下不停变换长度
--在昨晚凌乱的梦里,Darrel打开了伸向他的那只手。
日子恢复了本来面目,生活继续变得波澜不惊。
教学楼搬到食堂旁边。班主任喜滋滋地说现在离食堂近了,可方便你们了。言下之意是:"你们除了吃饭睡觉,都给我待在教室里学习。"
与寝室室友的关系一直没有好转。每天晚上他们用被子蒙住身体,趴在床上学习。因为怕舍管员的训斥,哪怕从被子的罅隙里泻出一点光,也会互相小声提醒。而那时我平躺在床上,耳机里盘旋的全是Darrel的歌声,陷入长长短短的梦境。
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不一样。
不得不忍受宿舍里跑鞋浓重的臭味。忍受每天晨练时绕教学楼长跑,同班同学因为厌烦,在队伍里用方言响亮地叫骂。
与此同时我开始想念深原,想念阿Z,想念假期每一个打工的日子。然而每夜我藏在被子里,调出手机通讯录里阿Z的号码,盯着白花花的屏幕很久,一直到眼生疼,却不知该编辑什么短信给他。
开学半个月后的周六,熄灯后我偷偷溜出校门,去灯光明亮的深原。
还是老路,幽径。公园的植物营造出与夜色相融合的深沉环境。我看到覆盖如墙的绿色藤蔓,深原的光隐隐约约透过来。
我熟门熟路地收拾茶具,清洗茶垢。阿Z见我没显露一点惊讶,还是轻轻拍我的肩,口角淡淡地说:"你来了。"
那夜忙到很晚。等服务生都走光,阿Z关闭深原所有的灯,和我坐在喷泉旁。
"如果有时间,还是来帮帮忙吧。"他对我说,"工资的事,我会和我爸谈妥的。"
我点点头。在黑暗里,不知他能不能看见。深原这座楼,忽然显得格外巨大。没有白天的喧嚣,它露出安静的轮廓。
因为有了寄托,每一天不再那么漫长。
每个周六的夜晚都会翻墙出校门。若不去深原打工,就到学校周围的网吧,尽一切可能搜寻Darrel的信息。或趴在屏幕前,整晚整晚看他的视频。
小A上传的那个视频点击率一直很高。美中不足的是在Darrel看向这边、离镜头很近的时候,画面晃动得厉害,而且忽然就戛然而止了。
网友纷纷留言,责问为什么停止。但小A一直不予回应。时间一久,人们关注的热点又转到Darrel的外形、唱功上了。
夏末的最后一场雨过去,所有的知了都销声匿迹。偶尔听见蛐蛐的鸣叫,夜晚时,听来像是模糊的呓语。
穿上厚衣的第二天去深原帮忙。一客人冒冒失失地把我手里的壶碰撒了,茶水大半都溅在我胳膊上。阿Z急忙把我的外套拽下来,把我拖到水池旁,用自来水冲洗。我呲牙咧嘴地说没事,尽量做出笑的表情。被烫的地方露出鲜红色。我半边身子都湿了,狼狈地打着哆嗦。
他居然笑了。我皱一皱眉,问他你笑什么。
"我一直奇怪,"他说,"你又不缺钱,来打工遭这份罪干嘛?"
"谁说我不缺钱,"我接过毛巾擦胳膊,抬眼看他,顿一顿又说:"我要攒钱去英国看Darrel的演唱会。"
隔几天我在学校收到阿Z快递的包裹。
"这是我托朋友从英国寄过来的。"他留言。
我拆开,是一本很厚的时尚杂志,每一页都是极富质感的铜版纸。长篇累牍的英文,搭配Darrel扎眼的写真。依然是海蓝色的眼睛,狭长的眉毛,笑起来嘴角的皱褶很迷人。
我趴在床上用电子词典把蹩脚的英文逐个翻译过来。睡在靠窗位置,窗户一直大开。秋天略带寒意的风卷进屋子,始终懒得去关。
用了很长时间,看到周身发冷。我确定一个事实:Darrel要退出歌坛,在自己家乡举办最后一场演唱会。
我不止一次登上学校的教学楼,俯瞰我身处的这个世界。
学校形状是规规矩矩的四方形,用巨大石块砌成的围墙,阻断与外界的联系。教学楼前辟出一大块空地,据说将用来修广场。褐黄色的土地,像老年人的秃斑。
空地一角堆满垃圾。风吹来时,随黄土大面积扩散。
唯一的几簇树木,在风里瑟瑟发抖,很快被沙土和垃圾覆盖。
生命在这种压抑的方式下苟延残喘。
最近去深原的时候,阿Z给了我一封信。他把我拉到角落里,神秘兮兮地说:"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一个女生?"他向我描述女生的长相、穿着,我大略知道了是谁。是隔壁班很显眼的女生。
"把信给她,"他的呼吸有点急促,"那女生住在我家附近。看校徽知道你们是一个学校的。把信给她行吗?"
我看看手里的信。信封是很浅的粉红色,隐约能看出心的形状。我明白这是什么。
回学校后,用手电筒照信封。想撑开信封的纤维看清里面的字。明明知道是什么却不敢承认,明明……
我想起学校里那几棵树,生命只是在苟延残喘,空虚和无力感占据了我的身体。
--我想去英国。
--我要去看Darrel最后一场演唱会。
不管怎样,我决定要离开了。
拜托同学把信交给隔壁班的女生。他们接过信时用奇怪的表情看我,发出阴阳怪调的声音:"看不出来啊,你……"
"这是我哥哥的。"我不耐烦地打断他们。从钱包里拿出Darrel的照片摆弄。
从阿Z给我信后,我增加了去深原的次数,有时上课日的晚上也偷偷溜出去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。
无限接近一个巨大的事实,却惊愕地不敢开口。
或者去网吧,努力撑着眼皮,通宵看Darrel的视频。有时趴在屏幕前睡着了,醒后满嘴苦涩的味道。全身沾满香烟浓重的臭味,我踉踉跄跄地从椅子上站起来,烟味直往鼻子里钻,我忍不住皱紧眉头。
或许是我太没节制,在课上不停睡觉,眼圈周围扩散的黑色日益剧增。也可能是寝室里某个人告了密。我从网吧归来的途中被班主任截住了。
他在我面前,掐着腰:"叫你家长来吧。"
我说我爸妈在外地,来不了。
"那你有监护人吗?"他拉开椅子,坐下。用手指击桌面,明显看出不耐烦。
一瞬间我想起了阿Z。
我称阿Z为哥哥。他低着头忍受完班主任的训斥,去寝室帮我收拾好东西。按学校规定,擅自外出要停课半月。
他用手握住我的小臂,拖着我的行李箱在前面走。
"你没有告诉我,你每次来深原都是从学校逃出来的。"他低下头,"你应该告诉我。"
我张张嘴,不知该对他说什么。秋天的风鼓满他的衣服。他瘦削的身体,他在夕阳下欣长的影子。我摇摇头,无边的悲伤笼罩着我。
我的脾气开始变得反复无常。在家里的时间,奉献给无尽的恍惚和睡眠。偶尔清醒,把耳机围在脖子上。Darrel的新歌,一遍又一遍听。
树叶一层层往下落,踩上去嘎吱嘎吱。秋末时节,很适合胡思乱想。思想太轻,在深原、阿Z和Darrel之间晃来晃去。
天光变暗后踏上去深原的路。因为变冷,客人逐渐稀落下来。有时灯光漫溢到四处,屋里只有寥寥的人。
"这是淡季啊。"阿Z对我说,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什么。他偶尔也会向我问起Darrel,他没有我的痴迷,大约连他的歌名都叫不全。阿Z的疑惑只是我对他死守的坚定。可这奇怪的情感连我自己也说不清。
阿Z一直帮我计算日子,计算我离回校的时间。"很快了,"一个黄昏他笑着对我说,"你啊,还是回学校好。你适合那里的生活。"
我不置可否。然而也是在那天,我因为一点小事差点和客人吵起来。自己一直很谦卑,尽量满足那桌客人的要求。然而他们一直不中意环境,屡次要求换桌,嫌弃这不干净、那没收拾好。我把茶壶摔在桌上:"到底要怎样你们他妈的才满意。"
那帮男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。阿Z赶紧跑过来,小声说着:"几位叔叔有话好好说,这是新来的,不懂事。"他陪着笑,把我推到一边。我抬眼向外望去,喷泉粼粼的水面,开始结冰了。
这种事往后又发生几次。我不知怎么了。身体的内核仿佛在燃烧,手脚却一直很冰凉,凉到我拿起茶杯,手就会发抖。
在我离回校还有两天时,茶楼里来了一大群女生。给别桌客人倒茶时,听到她们隐隐约约的叫骂。我回过身,看那帮女生把阿Z围起来。
"你别不要脸了。""你给我们家小清写什么信呐,你不看看自己的这副样子。""算什么东西啊。"
类似的骂声从人堆里传过来。茶楼的人纷纷起身,看出了什么事。我隐约知道发生什么,攥着脏乎乎的衣角,手抖得更厉害。
好久女生散去,阿Z一直站在原地。他没与她们争吵,只是默默忍受。
"阿Z……"我走到他身边,轻声轻气地叫他。
"好了,你别说了。"他抬起双手,苦涩的笑容蔓延开来。
"这个样子,叫我不知如何是好了……"
天气越来越冷,简陋的宿舍像冰窖一样。每晚都被冻醒,摸着冰凉的笔尖,窗户被蒙上大片水汽。外面的灯光透进来,似乎下了一场雾。
我买了暖水袋。只是下半夜暖水袋也会变凉。因为太冷,睁着双眼一直到天亮,怎么也睡不着。
我托网友替我查了去英国看Darrel演唱会的价钱。在上课时接到短信,我低头看到屏幕上一连串的零,又摸摸自己的钱包,信用卡里有阿Z刚给我打上的工资。
忽然感觉自己很可笑。以至于在上课时笑出声音,把老师同学的目光都招致过来。冬天干燥的嘴唇,一笑就会撕裂。我伸出舌头,把腥甜的血舔进嘴里,轻轻咽下去。
那夜我做了个梦。梦里站在灯光舞台上唱歌的不是Darrel,是阿Z。他没有狭长的眉毛,没有海蓝色的眼睛,没有笑起来迷人的皱褶。
但他有温暖的笑。他迎着台下的万般宠爱唯独注视着我。对视了一刻,是非常美好,非常安静,想起来叫人想落泪的一刻。
醒后枕头上一片潮湿。水袋不知怎么破了,水泻在胸膛上。冬天里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似乎要结上霜。
我把身子侧过去,怔怔地面向墙。咬紧牙,眼泪还是落了下来。
演唱会开始的前三天,我在网上通过一切关系联系到小A。我只是在困惑,那个忽然熄灭的镜头。
起初他不肯说,支支吾吾地应付我,屏幕上满是成串的省略号。后来被我逼烦了,他给我发来信息:"好吧,我告诉你,我想给Darrel握手的,但他不知为什么,一下子把我的手打开了。我说,别再喜欢这些乱七八糟的明星了。咱们啊,还是现实一点吧。"
我迎着电脑的屏光掏出Darrel的照片,忽然感到陌生且遥远。
那一刻觉得,和阿Z一比,你Darrel什么都不是。
"对不起,"我给阿Z发送短信,"对不起。"屏幕上只有这几个字。
一会儿手机亮起来:"天亮后来深原吧。我等着你。"
我起身,窗外冬天的夜空晴朗且干燥。想起了一首好听的歌,却不是Darrel的。我闭上眼睛,接着小声唱起来。
阿Z,我看到你对我招手。你的身后是一整个被风吹拂、几欲倾斜过来的巨大草原。
大风吹过,繁星欲坠。
除特别声明为原创作品以外,本站有部分文章、数据、图片来自互联网,一切转载作品其版权均归源网站或源作者所有。
如果侵犯了你的权益请来信告知我们删除。邮箱:116169014@qq.com
上一篇:过客于尘世间,人生的浮华